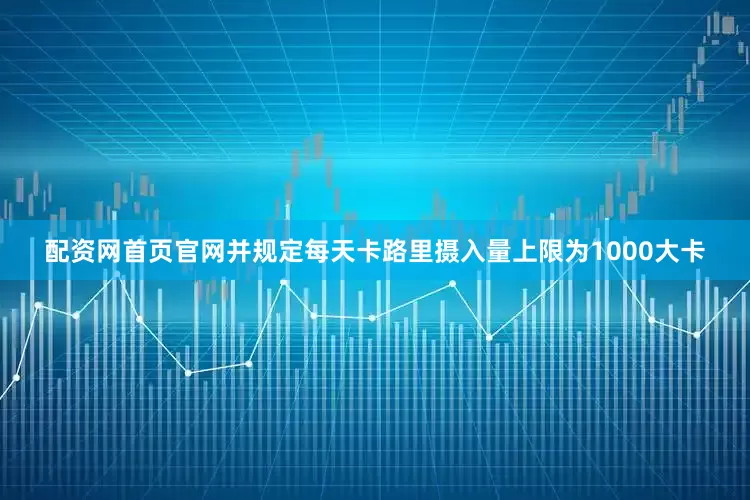参考来源:《清史稿》、《康熙朝起居注》等相关史料,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紫禁城,养心殿的更漏在无声地滴答。
殿外是康熙四十七年的深秋,寒鸦在枯枝上嘶哑地叫着,声音穿不透厚重的殿墙。
殿内,一灯如豆,映着四阿哥胤禛那张永远看不出波澜的脸。
写的不是诗词,不是文章,而是一遍又一遍的“戒急用忍”。
这四个字,他已经写了整整一个时辰。
每一笔,都像是用刻刀在骨头上划过,力道沉稳,锋芒内敛。
门外传来极轻的脚步声,是他的贴身太监苏培盛。
“主子,”苏培盛的声音压得极低,仿佛怕惊扰了空气中凝结的霜,“万岁爷赏了东西下来。”
胤禛的笔尖微微一顿,随即恢复如常,直到写完最后一笔,才缓缓抬起头。
“什么东西?”他的声音和他的人一样,冷得像一块冰。
苏培着捧上一个紫檀木的托盘,上面盖着明黄色的绸布。
绸布揭开,里面不是金银玉器,也不是珍本书画,而是一把极为普通的木梳。
梳子已经很旧了,梳齿圆润,显然是被人常年使用,摩挲得油光发亮。
胤禛的瞳孔猛地一缩。
这把梳子,他认得。
是皇阿玛年轻时,孝诚仁皇后亲手为他雕的。
是康熙皇帝用了几十年的随身之物。
在太子胤礽被废,诸皇子蠢蠢欲动,京城风雨欲来的这个当口,皇阿玛为何要把这把代表着“结发”与“顺”的旧物,赏给自己?
苏培盛不敢多言,只是将托盘又往前递了递。
胤禛伸出手,指尖触到木梳的瞬间,一股彻骨的寒意从指尖瞬间窜遍全身。
他明白了。
这不是赏赐。
这是警告,是敲打,更是一场无声的考验。
皇阿MA在用这把梳子告诉他,也告诉所有人:天下,还是他爱新觉罗玄烨的。
而他们这些儿子,无论是谁,都必须像这把梳子一样,顺着他的心意,梳理这大清的天下。
谁敢生出乱麻,谁就会被第一个折断。
胤禛缓缓闭上眼睛,再睁开时,眼中已是一片死水般的平静。
他拿起那把木梳,对着灯火,一下,一下,极慢地梳理着自己的发辫。
动作一丝不苟,仿佛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
寒夜,还很长。

01
康熙四十七年,是一个多事之秋。
先是黄河决堤,泛滥千里。
紧接着,太子胤礽在围场行径荒唐,终于触怒了康熙,被废黜圈禁。
这道谕旨,如同一块巨石砸入看似平静的湖面,激起了滔天巨浪。
大清的皇子们,第一次发现,原来头顶那座不可动摇的大山,也是可以被搬开的。
一时间,紫禁城内外的空气都变得滚烫而粘稠。
人心,开始浮动。
其中,最活跃的莫过于八阿哥胤禩。
胤禩素有“八贤王”之名,为人谦和,礼贤下士,在朝野上下都颇有声望。
太子被废,他便成了众望所归的新储君人选。
他的府邸,一时间门庭若市,车马喧嚣。
相比之下,四阿哥胤禛的雍王府,则显得门可罗雀,冷清异常。
胤禛似乎对储位之争毫无兴趣。
他每日除了上朝,便是在府中修身养性,侍弄花草,或是与几个门人清谈。
他将自己活成了一个真正的“闲散王爷”。
这日,胤禛正在书房临摹一幅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
他的嫡福晋乌拉那拉氏端着一碗参汤,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
“爷,歇会儿吧。”她将参汤放在桌上,轻声说道。
胤禛没有抬头,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
乌拉那拉氏看着丈夫专注的侧脸,棱角分明,却也透着一股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
她犹豫了片刻,还是忍不住开了口:“爷,如今外面都在传,说万岁爷属意八弟……”
“啪”的一声,胤禛手中的毛笔重重地砸在了砚台上,墨汁四溅。
乌拉那拉氏吓了一跳,噤若寒蝉。
“妇道人家,不要妄议朝政。”胤禛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喙的威严。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负手而立。
窗外,秋风萧瑟,卷起几片枯黄的落叶。
他的内心,远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平静。
他何尝不知道外面的风言风语?
他何尝感觉不到兄弟们那灼人的目光?
只是,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们的那位皇阿玛,是何等雄才大略,又是何等猜忌多疑。
在玄烨的眼中,儿子首先是臣子,然后才是儿子。
他允许儿子们优秀,但绝不允许任何人的优秀,威胁到他的皇权。
他做了三十多年的太子,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为何倒台?
不是因为他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他太急于证明自己的优秀,急于将储君的权力,变成真正的权力。
他忘记了,只要皇阿玛还在一天,这天下就只有一个太阳。
而现在,八弟胤禩正在重蹈覆辙。
他那所谓的“贤名”,那门庭若市的盛况,在胤禛看来,不过是催命的符咒。
皇阿玛需要的是一个能干的臣子,一个听话的儿子,而不是一个觊觎他御座的潜在威胁。
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这是皇阿玛最痛恨的事情。
胤禛闭上眼,深吸一口气。
他知道,自己必须等。
等八弟他们尽情地表演,等他们将所有的野心都暴露在阳光下。
等皇阿玛对他们彻底失望。
他要做的,不是去争,而是去做一个皇阿玛眼中最完美的工具。
一个没有感情,没有派系,只有忠诚和能力的工具。
夜色渐深,胤禛遣散了下人,独自一人来到书房的密室。
密室里,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一排排的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卷宗。
这些卷宗,记录的不是经史子集,而是从黄河水利到边疆军备,从朝廷赋税到各地民情的详细资料。
每一本,都有他亲手写下的批注和心得。
这是他耗费了十几年心血,建立起来的“数据库”。
他不像八弟那样,用笑脸和恩惠去笼络人心。
他用的是最笨,也是最扎实的办法——做事。
康熙交给他的每一件差事,无论大小,他都办得妥妥帖帖,无可挑剔。
他要让皇阿玛知道,这满朝的儿子里,只有他,才是那个真正能为大清江山分忧的人。
就在此时,密室的门被轻轻敲响。
能进入这里的,只有一个人——他最信任的谋士,戴铎。
“主子,”戴铎的声音里透着一丝焦急,主子,”戴铎的声音里透着一丝焦急,“八爷那边,又有新动静了。”
胤禛转过身,脸上依旧是那副冰冷的表情。
“说。”
“大阿哥上书,奏请诛杀废太子,朝中附议者甚众。而八爷……他虽未明言,却暗中让人联络九爷、十爷他们,准备联名上书,保举他为新太子。”
胤禛的嘴角,勾起一抹几乎看不见的冷笑。
真是愚蠢。
大阿哥胤禔这是在自掘坟墓。
而八弟胤禩,更是将自己的野心,赤裸裸地摆在了皇阿玛的面前。
他难道忘了,皇阿玛虽然废了太子,但对胤礽的父子之情犹在?
在这个时候逼迫皇阿玛,只会引火烧身。
“由他们去吧,”胤禛淡淡地说道,由他们去吧,”胤禛淡淡地说道,“风,还不够大。”
他需要一场更大的风暴,一场足以将所有不安分的兄弟们,都卷进去的风暴。
只有当所有人都倒下的时候,那个始终屹立不倒的人,才会最终被看见。
而他,就要做那个最后站着的人。

02
风暴,比胤禛预想的来得更快,也更猛烈。
康熙皇帝看到大阿哥请求诛杀胤礽的奏折后,雷霆震怒。
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痛斥胤禔“不忠不孝,残忍悖逆”,将其圈禁。
紧接着,他又将矛头对准了结党营私的八阿哥胤禩。
“朕未尝言立新太子,胤禩何得人心,为其所推戴?”
这句问话,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胤禩和他的党羽心上。
康熙下令,严查此事。
一时间,朝野震动,人人自危。
曾经门庭若市的八王府,瞬间变得冷清下来。
那些曾经围着胤禩摇尾乞怜的官员,如今都对他避之不及。
一场声势浩大的“八爷党”倾覆记,就此拉开序幕。
胤禛依旧待在自己的王府里,不动如山。
但他并非什么都没做。
他通过戴铎,将胤禩一党结交朝臣、收受贿赂的证据,不着痕迹地送到了康熙的案头。
他没有落井下石,没有一句弹劾之语。
他只是将事实摆在那里。
他知道,以皇阿玛的精明,自然会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果然,康熙在看到那些证据后,对胤禩彻底失望。
他下谕,斥责胤禩“柔奸成性,妄蓄大志”,削其爵位,罚其闭门思过。
“八贤王”的神话,一夜之间破灭。
处理完这些跳得最欢的儿子,康熙似乎也感到了一丝疲惫。
他没有急于册立新的太子。
皇储之位,就此悬空。
这反而让局势变得更加诡异莫测。
剩下的皇子们,虽然不敢再像胤禩那样明目张胆地拉帮结派,但暗地里的较量,却从未停止。
他们每个人,都像是在黑暗中潜行的猎手,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踪迹,同时又死死地盯着那唯一的猎物。
十四阿哥胤禵,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个。
他与胤禛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但两人的关系却势同水火。
胤禵自幼在康熙身边长大,能文能武,性格豪爽,深得康熙喜爱。
尤其是在军事上,他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
康熙常常将他带在身边,亲自教导他排兵布阵之法。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康熙正在将胤禵,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将帅之才。
这让许多人猜测,康熙是不是有意让胤禵,走一条“武立”的路子。
毕竟,大清是靠弓马得的天下。
一个能征善战的皇帝,远比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皇帝,更让人信服。
胤禛敏锐地感觉到了来自这个亲弟弟的威胁。
但他依旧没有轻举妄动。
他知道,皇阿玛虽然欣赏胤禵的军事才能,但也同样忌惮一个手握重兵的皇子。
权力,必须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中。
任何可能分享这种权力的存在,都是潜在的威胁。
胤禛继续着自己的“孤臣”之道。
他默默地接手了户部的烂摊子。
当时的户部,因为连年战事和天灾,国库空虚,亏空严重。
胤禛却主动请缨。
他一上任,便展现出了铁血无情的手腕。
他下令彻查亏空,追缴欠款。
无论涉及到谁,哪怕是皇亲国戚,也绝不姑息。
一时间,京城上下,怨声载道。
许多人都在背后骂他是“冷面王爷”,不近人情。
甚至有人跑到康熙面前告状,说他刻薄寡恩,有失皇家体面。
康熙每次都只是笑而不语。
但他心里,却比谁都清楚。
国库的亏空,是他的一块心病。
这些年,他不是不想整顿,只是投鼠忌器,怕引起太大的动荡。
而现在,老四替他做了他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这个儿子,虽然性子冷了些,却是一把最好用的刀。
一把能为他斩断一切沉疴顽疾的利刃。
一日,康熙在畅春园设宴,召集了几个年长的皇子。
酒过三巡,康熙忽然开口问道:“胤禛,朕听说,你在户部得罪了不少人啊。”
众皇子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胤禛身上,大多带着幸灾乐祸的意味。
胤禛放下酒杯,离席跪倒在地。
“儿臣不敢。儿臣只是在为皇阿玛分忧,为大清的江山社稷尽一份心力。追缴亏空,是为国,非为私。若因此得罪了人,儿臣也无怨无悔。”
他的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晰,掷地有声。
康熙定定地看了他半晌,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好一个无怨无悔!”
他走下御座,亲手将胤禛扶起。
“有你这样的儿子,朕心甚慰。”
说完,他拍了拍胤禛的肩膀,转身离去。
留下满屋子的皇子,面面相觑,神色各异。
尤其是十四阿哥胤禵,他看着胤禛的背影,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有嫉妒,有不甘,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恐惧。
他忽然发现,自己似乎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这个四哥。
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只知埋头办差的兄长,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到了所有人的前面。
他不像八哥那样,需要用“贤名”来装点自己。
也不像自己这样,需要用战功来证明价值。
他只用最纯粹的“能力”,就赢得了皇阿玛的另眼相看。
这是一种更高明的,也更可怕的争夺方式。
胤禵的心中,第一次生出了强烈的危机感。
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了。
他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西北边疆。
那里,准噶尔部正在蠢蠢欲动,威胁着大清的安宁。
对他来说,那既是危险,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个建立不世之功,彻底压倒四哥的机会。
一场围绕着军功和政绩的无声竞赛,在兄弟二人之间,悄然展开。

03
康熙五十七年,西北战事吃紧。
康熙皇帝决定,派遣一位皇子出任抚远大将军,统领大军,西征准噶尔。
消息一出,整个朝堂都沸腾了。
所有人都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军事任命。
这更像是一场储位之争的终极考验。
谁能拿下这个位置,谁能打赢这场仗,谁就最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大清之主。
十四阿哥胤禵,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
他本就是军中宿将,这些年又屡立战功,无论资历还是能力,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朝中大部分的官员,也都支持他。
康熙似乎也对他青睐有加。
他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胤禵“深肖朕躬”,是天生的将才。
一时间,胤禵的风头,甚至盖过了当年的八阿哥胤禩。
他仿佛已经将那顶耀眼的皇冠,提前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出征前夕,康熙在太和殿前,为胤禵举行了异常隆重的欢送仪式。
他亲手将帅印交到胤禵手中,并允许他使用“天子旌旗”。
这是何等的荣耀!
在大清的历史上,只有皇帝亲征,才能使用这样的仪仗。
康熙此举,无异于是在向天下宣告,胤禵就是他的影子,是他最信任的继承人。
胤禵身披铠甲,跪在地上,双手高高举起,接过了那方沉甸甸的帅印。
他的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和自豪。
他转过头,目光扫过前来送行的兄弟们。
当他的视线落在四阿哥胤禛身上时,他看到的是一张毫无表情的脸。
没有祝贺,没有嫉妒,只有一如既往的冰冷。
胤禵的心中,闪过一丝不屑。
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四哥,恐怕这辈子都只能当一个埋首于钱粮文书的酷吏了。
而他,将要策马扬鞭,在广阔的战场上,为自己,也为大清,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
大军开拔,浩浩荡荡。
京城的目光,都随着胤禵的背影,一路向西。
所有人都认为,储位之争,已经尘埃落定。
只有胤禛,依旧平静地处理着户部的事务。
仿佛这场关乎国运和皇权归属的巨大变动,与他毫无关系。
戴铎看着他,心中充满了忧虑。
“主子,难道我们就这样坐以待毙吗?”他忍不住问道。
胤禛放下手中的账本,抬起头,目光深邃如海。
“你觉得,皇阿玛为何要给十四弟如此高的规格?”
戴铎一愣,随即答道:“自然是为了彰显皇恩,激励他奋勇杀敌。”
胤禛摇了摇头。
“这只是其一。”
他走到一张巨大的地图前,手指点在了西北边疆的位置。
“皇阿玛此举,既是给十四弟的荣耀,也是给他套上的枷锁。”
“枷锁?”戴铎不解。
“你想想,’天子旌旗’一出,代表的就是皇阿玛亲临。这一仗,只能胜,不能败。一旦战事稍有不顺,罪责就会比寻常将领大上百倍。因为他丢的,不仅仅是大清的脸面,更是皇阿玛的脸面。”
胤禛的声音很轻,却让戴铎感到一阵寒意。
“而且,大军在外,粮草先行。如今国库并不充裕,西北路途遥远,后勤补给的压力,会非常巨大。这仗,打得越久,对国力的消耗就越大。”
戴铎似乎明白了什么。
“主子的意思是……这一仗,并不好打?”
“不是不好打,是皇阿玛根本不希望他打得太顺,太快。”
胤禛的眼中,闪过一丝洞悉一切的锐利光芒。
“皇阿玛需要西北的战事,来牵制十四弟。只要大军还在前线,他就永远只是一个手握兵权的将军,而不是一个可以威胁皇权的储君。皇阿玛要的,是一个能打仗的儿子,但绝不是一个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藩王。”
“这……这就是制衡之术?”戴铎倒吸一口凉气。
“没错。”胤禛缓缓点头,没错。”胤禛缓缓点头,“皇阿玛这一生,都在玩弄制衡之术。他对付大臣是如此,对付我们这些儿子,同样如此。”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你以为,这天下,真的有那么多人敢和我们争储吗?康熙三十五个儿子,成年的有二十个。可你看看,真正跳出来的,有几个?”
“从老大胤禔,到老二胤礽,再到老八胤禩,他们哪个不是被皇阿玛捧得高高的,然后又亲手摔得粉碎?”
“皇阿玛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所有人:他可以给你一切,也可以随时收回一切。他的恩宠,是蜜糖,也是最致命的毒药。”
“大多数兄弟,早就看透了这一点。他们不敢争,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野心,而是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害怕成为下一个胤礽,下一个胤禩。”
“他们宁愿选择当一个富贵闲人,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也不愿意去赌那万分之一的机会。因为赌输的下场,就是万劫不复。”
胤禛的声音在密室中回荡,每一个字,都像是冰冷的铁锤,敲打在戴铎的心上。
戴铎终于明白,自己这位主子,为何始终如此隐忍,如此低调。
他不是不争,他只是在用一种别人看不懂的方式在争。
他争的,不是一时的恩宠和声望。
他争的,是皇阿玛心中那个最“稳妥”,最稳妥”,最“可靠”的位置。
当所有人都被欲望冲昏头脑,在前台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他却悄悄地走进了后台,试图去理解那个唯一的,也是最终的裁判。
就在这时,一个负责情报的下属匆匆进来,递上了一份密报。
胤禛打开密报,只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密报上只有短短一行字。
“圣体违和,上疾复发。”
康熙的身体,不行了。
戴铎也看到了那行字,脸色瞬间煞白。
“主子,这……”
胤禛没有说话,他快步走到书案前,提笔写了一封奏折。
奏折的内容很简单,请求皇阿玛保重龙体,同时,他愿意代父出巡,去天坛为圣上祈福。
“立刻送出去。
戴铎接过奏折,心中却充满了疑惑。
这个时候,不应该想办法留在京城,留在康熙身边,以防万一吗?
为何主子反而要主动请求离开?
去天坛祈福?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一个远离权力中心的举动。
胤禛看出了他的疑惑,却没时间解释。
他只说了一句:“快去。记住,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是我主动请缨的。”
戴铎不敢多问,领命而去。
密室里,又只剩下胤禛一个人。
他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动弹。
他知道,自己刚刚走了一步险棋。
但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棋。
皇阿玛生性多疑,尤其是在他病重的时候。
此刻,任何一个留在京城,表现出对权力过于渴望的儿子,都会引起他最大的警惕。
而他,主动请求离开,去为父亲祈福。
这是一种姿态。
一种“我心无私,只念父子之情”的姿态。
这能最大限度地打消皇阿玛对他的猜忌。
同时,天坛,这个看似远离中心的地方,实际上却是一个信息汇集的枢纽。
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暂时脱离紫禁城的漩涡,冷静地观察局势,并暗中布置一切。
更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的这一举动,皇阿玛一定能看懂。
在所有的儿子都盯着他那把龙椅的时候,只有老四,还在关心他的身体。
这种“孝心”,在此时此刻,比任何政绩和军功,都来得更加重要。
然而,胤禛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惊天的秘密,正在暗中浮现。
一个足以颠覆整个夺嫡之争,甚至改变大清国运的巨大阴谋。
数日后,就在胤禛于天坛斋戒之时,苏培盛深夜匆匆赶来,神色慌张到了极点。
他递给胤禛一张字条,是从宫里一个极可靠的线人那里传出来的。
胤禛展开字条,上面画着一个诡异的图案,图案旁边,写着三个字。
“粘杆处”。
04
粘杆处。
这三个字,像一道黑色的闪电,瞬间劈开了胤禛脑中的迷雾。
对于这个名字,他并不陌生。
宫中一直有传闻,说这是一个由皇帝直接掌控的秘密组织,如同黑夜中的幽灵,监视着宫内宫外的一举一动。
但它究竟是怎样一个存在,由谁组成,权力有多大,却无人知晓。
它就像悬在每个人头顶的一把隐形利剑,你不知道它何时会落下。
而现在,这个名字,竟然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胤禛立刻意识到,这张字条的背后,隐藏着天大的玄机。
他将苏培盛带入密室,沉声问道:“说,到底怎么回事?”
苏培盛的声音都在发抖:“主子,宫里的线人说,最近粘杆处的人,活动异常频繁。他们……他们似乎在调查一件和废太子有关的旧案。”
“旧案?”胤禛的眉头紧紧锁起。
“是。据说,是关于当年大阿哥魇镇废太子的事情。”
魇镇,是一种用巫蛊之术害人的邪术。
当年,康熙废黜太子胤礽,其中一个重要的罪名,就是大阿哥胤禔用魇镇之术,使得胤礽言行失常,疯癫悖逆。
此事当初闹得沸沸扬扬,胤禔也因此被终身圈禁。
这早已是铁案,为何粘杆处要在这个时候,重新翻出来调查?
胤禛在密室中来回踱步,大脑飞速地运转。
一个大胆到让他自己都感到心惊的猜测,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难道……当年的魇镇案,另有隐情?
如果说,胤礽的疯癫,并非完全是大阿哥所为,那背后,是否还有其他的推手?
皇阿玛是何等英明神武的君主,他真的会被区区魇镇之术蒙蔽吗?
还是说,他当初只是顺水推舟,利用这个由头,废掉那个已经让他感到威胁的太子?
胤禛越想,背后的冷汗就越多。
他忽然明白,皇阿玛的制衡手段,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和狠辣。
所谓的“九子夺嫡”,从一开始,或许就是康熙亲手导演的一场大戏。
他故意制造出储位悬空的局面,引诱儿子们互相争斗,彼此消耗。
他就像一个最高明的棋手,看着棋盘上的棋子们互相厮杀,而他,则在暗中观察着每一个棋子的心性、能力和弱点。
他废掉太子,不是因为太子无能,而是因为太子的势力已经大到让他感到不安。
他打压八爷党,不是因为胤禩不贤,而是因为胤禩的声望,已经开始挑战他的权威。
他重用十四弟,也不是真的想让他继承大统,而是需要他去平衡朝中的文官势力,并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将他牢牢地拴在边疆。
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皇权的绝对集中。
而粘杆处,就是他用来掌控全局,清除一切潜在威胁的最锋利的刀。
这个组织,恐怕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渗透到了各个王府,甚至安插在了他们这些皇子的身边。
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或许都在皇阿玛的监视之下。
想通了这一层,胤禛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
他 এতদিন自以为的隐忍和低调,在皇阿玛的眼中,或许也只是一场心机深沉的表演。
那么,皇阿玛对自己,到底是什么态度?
是欣赏?是利用?还是……早已暗中提防?
就在胤禛心乱如麻之际,苏培盛又递上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份名单。
名单上,罗列着数十个官员的名字。
这些人,有的是八爷党的余孽,有的是十四弟的亲信,还有一些,则是平日里看似中立的朝中大员。
“这是?”胤禛不解地问。
“这是粘杆处接下来要‘清理’的名单。”苏培盛的声音压得更低了,这是粘杆处接下来要‘清理’的名单。”苏培盛的声音压得更低了,“线人说,皇上的意思是,要在龙驭上宾之前,为新君扫清一切障碍。”
胤禛的心,猛地一沉。
为新君扫清障碍?
皇阿玛,已经选定了继承人?
会是谁?
是远在西北的十四弟胤禵?
还是……自己?
他死死地盯着那份名单,试图从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他发现,名单上的人,虽然派系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他们都是朝中势力盘根错节,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如果这些人被清除,那么无论谁继位,都将面对一个被大大削弱了的官僚集团。
新君将能够更容易地,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这确实是在为新君铺路。
但皇阿玛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
胤禛忽然想起了那把旧木梳。
顺。
皇阿玛要的,是一个能“顺”着他的意愿,将他开创的集权统治,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的继承人。
这个人,不能有太强大的个人势力,不能有太复杂的派系背景,更不能有挑战皇权的野心。
他必须像一把梳子一样,简单,可靠,并且绝对忠诚。
胤禛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他看着名单,一个一个地往下看。
忽然,他的目光,停留在了名单的最后一个名字上。
隆科多。
当朝九门提督,康熙的亲表弟,也是胤禛的舅舅。
这个名字的出现,让胤禛的瞳孔,瞬间收缩成了针尖大小。
隆科多,手握京城九门的兵权,是京畿防务的最高负责人。
他虽然是自己的舅舅,但一直以来,都保持着绝对的中立,从未在储位之争中,偏向任何一方。
皇阿玛为何要动他?
还是说,这个名字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暗示?
一个巨大的谜团,笼罩在胤禛的心头。
他知道,自己已经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一步走错,就是万丈深渊。
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抉择。
是继续留在天坛,静观其变?
还是冒险返回京城,去探一探那深不可测的帝心?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密室的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一个侍卫在门外高声禀报:
“四爷!宫里来人了!是……是隆科多大人!他说,有万岁爷的口谕,要单独传给您!”

05
隆科多的到来,像是一阵风,吹散了天坛上空的宁静。
他穿着一身九门提督的官服,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但眼神中却透着一股不寻常的凝重。
他屏退了左右,只留下胤禛一人。
“四爷,万岁爷的口谕。”隆科多的声音低沉而沙哑。
胤禛跪下接旨。
“朕躬安。着四阿哥胤禛,于天坛好生祈福,不必挂念。京中一切,有朕在。”
短短的一句话,却让胤禛的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不必挂念”,不必挂念”,“有朕在”。
这听起来,像是宽慰,但以胤禛对皇阿MA的了解,这更像是一种警告。
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不要试图窥探京城的变故。
皇阿玛,似乎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好了。
而他,只需要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当一个孝子。
胤禛叩首谢恩,心中却充满了疑惑。
如果皇阿玛真的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为何还要特意派隆科多来传这样一句口谕?
难道,这口谕本身,就是一种试探?
他抬起头,看向隆科多。
他发现,自己的这位舅舅,在传完口谕后,并没有立刻离开的意思。
他只是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自己。
他的眼神,很复杂。
像是在传递某种信息,又像是在等待自己做出某种回应。
四目相对,空气仿佛凝固了。
胤禛的心中,闪过无数个念头。
他想起了那份粘杆处的名单。
想起了名单上,隆科多自己的名字。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的心中升起。
皇阿玛,是不是连隆科多,也不信任了?
派他来传这句口谕,或许就是为了测试他的忠诚。
测试他,究竟是忠于皇帝,还是忠于他这个外甥。
如果隆科多在传旨之外,对自己有任何多余的言语或暗示,那么等待他的,可能就是万劫不复的下场。
而自己,如果表现出任何想要拉拢隆科多的意图,也同样会触动皇阿玛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这是一个死局。
一个康熙用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为他们这些儿子设下的,最残酷的考验。
想通了这一层,胤禛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
他知道,自己不能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差错。
他缓缓站起身,对着隆科多,深深地作了一个揖。
“有劳舅舅跑这一趟了。皇阿玛圣体安康,是儿臣,也是大清子民最大的福分。请舅舅代为转告皇阿玛,儿臣一定谨遵圣谕,在天坛诚心祈祷,祝祷皇阿玛万寿无疆。”
他的语气,恭敬而疏离。
他称呼隆科多为“舅舅”,是念及亲情。
但他所说的话,却句句都是一个臣子,对君父的忠诚。
他没有问京城的情况,没有问皇阿玛的病情,更没有试图从隆科多的口中,套取任何信息。
他表现得,就像一个真正心无旁骛,只知孝道的儿子。
隆科多看着他,眼神中的复杂之色,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赞许。
他点了点头,同样回了一礼。
“四爷的孝心,万岁爷一定会知道的。卑职告退。”
说完,他转身,干脆利落地离去。
看着隆科多远去的背影,胤禛紧绷的神经,才终于有了一丝松懈。
他知道,自己赌对了。
他用最完美的表现,通过了皇阿玛的最后一道考验。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就在隆科多离开后不到半个时辰,苏培盛又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
这一次,他的脸上,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兴奋。
“主子!大喜啊!”
“何事惊慌?”胤禛皱了皱眉。
苏培盛从怀中,掏出了一件东西。
那是一块小小的玉佩,玉佩上,刻着一个“令”字。
这是九门提督的腰牌!
是隆科多的东西!
“这是……”胤禛的瞳孔猛地一缩。
“主子,刚才隆科多大人在出天坛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掉在了门口的石狮子底下。被我们的人捡到了。”苏培盛压低声音说道。
胤禛接过那块玉佩,入手一片冰凉。
他瞬间明白了。
这不是“不小心”掉的。
这是隆科多,故意留给他的。
隆科多用这种方式,向他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他,选择了自己!
可是,为什么?
皇阿玛明明已经将他列入了“清理”的名单,他为何还要冒着杀头的风险,向自己投诚?
难道……
胤禛的脑中,灵光一闪。
他忽然想明白了整件事的逻辑。
那份粘杆处的名单,或许根本就不是一份“清理”名单。
而是一份“托孤”名单!
皇阿玛并不是要杀了这些人。
他是用这种方式,将这些人,逼到新君的阵营里!
他深知,自己一旦驾崩,新君初立,根基不稳,必然会遭到各方势力的反扑。
尤其是那些手握重兵,或者是在朝中根深蒂固的旧臣。
而名单上的这些人,恰恰就是能够稳定局势的关键人物。
康熙用“死亡威胁”的方式,斩断了他们所有的退路。
他们唯一的活路,就是死心塌地地效忠新君,帮助新君坐稳江山。
因为只有新君,才能赦免他们的“罪行”。
好一招“置之死地而后生”!
好一个帝王心术!
胤禛手握着那块冰冷的玉佩,却感觉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
他终于彻底读懂了自己的父亲。
这位统治了中国六十一年的伟大帝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用他那无与伦比的智慧和谋略,为这个国家,为他的继承人,铺平最后一段道路。
他不仅选择了一个继承人。
他还为这个继承人,准备好了一个最忠诚,也最得力的班底。
而自己,胤禛,就是他选中的那个人!
所有的隐忍,所有的等待,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
他没有再犹豫。
他立刻召集了自己所有的心腹。
“传我的令,从现在开始,京城内外,所有我们的人,全部进入最高戒备状态。”
“戴铎,你立刻秘密联络步军统领衙门和丰台大营的人,告诉他们,时机已到。”
“苏培盛,你亲自去一趟畅春园,告诉年羹尧,让他看好园子里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八爷和九爷他们。”
一道道命令,从胤禛的口中,清晰而果断地发出。
这一刻,他不再是那个只知“戒急用忍”的冷面王爷。
他变成了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
天坛的钟声,悠悠响起。
一场决定大清未来命运的权力交接,已经拉开了序幕。
而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06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夜。
京城,畅春园。
康熙皇帝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这位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弥留之际,召见了隆科多和七位年长的皇子。
胤禛,也在其中。
寝宫内,烛火摇曳,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皇子们跪在床前,个个神情悲痛,但每个人的心里,都在等待着那个最终的宣判。
康熙躺在病榻上,呼吸微弱,浑浊的眼睛,缓缓地扫过跪在眼前的儿子们。
他的目光,在老三胤祉、老八胤禩等人的脸上一一掠过,最后,停留在了胤禛的脸上。
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却只发出了几个含糊不清的音节。
站在一旁的隆科多,立刻俯下身去,将耳朵凑到康熙的嘴边。
片刻之后,他直起身,转身面对众人,用一种沉重而清晰的声音,宣布了康熙的遗诏。
“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短短的一句话,如同九天之上的惊雷,在所有人的耳边炸响。
八阿哥胤禩的身体,猛地一颤,脸上血色尽褪,一片惨白。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怎么可能?
怎么会是老四?
他一直以为,自己即便不是首选,也至少是皇阿玛考虑过的人选。
而胤禛,这个在他看来毫无威胁的“冷面王爷”,竟然成了最终的胜利者。
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䄉等人,也都是一脸的错愕和不甘。
只有三阿哥胤祉,这个一向醉心于学术的皇子,脸上露出了释然的表情。
而胤禛,从始至终,都只是静静地跪在那里。
他的脸上,没有狂喜,没有激动,只有一种仿佛早已预知一切的平静。
他对着康死去的康熙,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
每一个,都无比沉重。
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的人生,将彻底改变。
他不再是四阿哥胤禛。
他是大清的新一任皇帝。
然而,皇位的交接,从来都不是念一道遗诏那么简单。
就在隆科多宣布遗诏的当晚,一股汹涌的暗流,便在京城之中涌动起来。
八爷党的核心成员,九阿哥胤禟和十阿哥胤䄉,连夜在府中密会。
他们不相信康熙会把皇位传给胤禛。
他们四处散播谣言,说胤禛勾结隆科多,篡改了遗诏。
甚至有传言说,康熙原本是想传位给十四子胤禵,遗诏上写的是“传位十四子”,被胤禛改成了传位十四子”,被胤禛改成了“传位于四子”。
这种说法,虽然荒诞不经,但在当时那个信息闭塞,人心惶惶的时刻,却极具煽动性。
一时间,关于新君得位不正的流言,传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一些原本支持十四阿哥胤禵的朝臣,也开始蠢蠢欲动。
他们希望能等到远在西北的胤禵回京,主持大局。
一场宫廷政变,似乎一触即发。
然而,他们都低估了胤禛,也低估了康熙为他留下的那份“遗产”。
就在流言四起的第二天凌晨,隆科多以九门提督的身份,宣布京城戒严。
步军统领衙门的九门兵马,在一夜之间,控制了京城所有的要害部门。
所有王公大臣的府邸,都被重兵“保护”了起来,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
紧接着,胤禛的另一位心腹,川陕总督年羹尧,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虽然身在畅春园,却早已通过胤禛的授意,掌控了园内的卫戍部队——丰台大营。
这支精锐的部队,将整个畅春园围得水泄不通,确保了康熙驾崩和遗诏宣布的核心区域,万无一失。
八阿哥、九阿哥等人,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实质性的举动,就发现自己已经成了笼中之鸟。
他们所能做的,就只剩下无能的狂怒和咒骂。
胤禛的手段,快、准、狠。
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彻底掌控了京城的局势。
他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所有人,他,爱新觉罗胤禛,就是大清名正言顺的皇帝。
任何试图挑战他权威的人,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稳定了京城之后,胤禛立刻着手处理下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隐患。
远在西北,手握十几万大军的亲弟弟,抚远大将军,胤禵。
所有人都认为,胤禛一定会立刻下令,解除胤禵的兵权,将他召回京城,加以囚禁。
然而,胤禛的做法,却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非但没有削夺胤禵的兵权,反而下了一道圣旨,对他大加封赏,肯定了他在西北的战功。
同时,他以皇帝的身份,命令胤禵,继续留在西北,主持军务,彻底平定准噶尔的叛乱。
这道圣旨,看似宽宏大量,实则歹毒无比。
这等于是将胤禵,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边将”。
他虽然手握重兵,但远离了政治中心。
只要胤禛牢牢掌控着朝廷的财政和人事大权,胤禵在前线的军队,就如同一个断了线的风筝。
粮草补给,军官任免,都必须经过皇帝的批准。
胤禛用一种看不见的方式,将套在胤禵脖子上的那根枷锁,收得更紧了。
胤禵在接到圣旨的那一刻,据说在军帐中,摔碎了自己最心爱的酒杯。
他明白,自己已经输了。
输得彻彻底底。
他纵有千军万马,但在绝对的皇权面前,也只不过是一个高级的囚徒而已。
至此,九子夺嫡的最后一场大戏,以胤禛的完胜,落下了帷幕。
那些曾经的竞争者,那些不敢和他争的兄弟们,也终于看清了一个事实。
他们不敢争,不仅仅是因为康熙的制衡手段有多高明。
更是因为,他们的对手,胤禛,是一个比他们所有人都更懂得权力游戏规则的,顶级玩家。
他隐忍,他蛰伏,他不动声色。
但在最关键的时刻,他能以雷霆万钧之势,扫平一切。
跟这样的人争,无异于以卵击石。
07
雍正元年,新皇登基。
紫禁城换了主人,但那股冰冷而肃杀的气息,似乎比康熙朝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皇帝胤禛,将他的“冷面”风格,贯彻到了治国理政的每一个角落。
他登基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查国库,追缴亏空。
这一次的力度,比他当年在户部时,还要大上十倍。
他设立了“会考府”,专门负责审计钱粮。
无数贪官污吏,在这场风暴中落马。
一时间,官场之上,人人自危,风声鹤唳。
他勤于政事,到了一个近乎自虐的程度。
据说,他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亲自批阅的奏折,动辄数千字。
从康熙朝后期开始的政务懈怠,官僚腐败的风气,被他用最强硬的手段,一点点地扭转过来。
那个曾经空虚的国库,在他的治理下,渐渐变得充盈。
他也加强了中央集权。
他设立了军机处,将国家的最高决策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那个曾经在暗中为康熙服务的“粘杆处”,也被他继承并扩大。
这个秘密的特务机构,成为了他监视天下臣民的眼睛和耳朵。
任何对他的统治构成威胁的言论和行为,都会遭到无情的打击。
文字狱,在他这一朝,也达到了顶峰。
他用严刑峻法,让天下所有的读书人,都闭上了嘴巴。
对于那些曾经的兄弟,他的处置,也同样冷酷无情。
八阿哥胤禩,被他削爵圈禁,改名为“阿其那”,意为阿其那”,意为“狗”。
九阿哥胤禟,被改名为“塞思黑”,意为塞思黑”,意为“猪”,最终折磨致死。
十四阿哥胤禵,也被召回京城,圈禁于景山,终其一生,都未能再获自由。
他用最残酷的方式,清算了所有的旧账,抹去了所有可能威胁他皇位的不安定因素。
他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
一个坐在权力之巅,拥有至高无上权威,却也承受着无边孤独的帝王。
一个深夜,雍正处理完一天的政务,感到一阵疲惫。
他让苏培盛,取来了一个紫檀木的盒子。
盒子里,放着那把康熙皇帝留给他的旧木梳。
他拿起木梳,对着铜镜,一下一下,梳理着自己已经有些斑白的头发。
镜中的那个人,面容清瘦,眼神锐利,嘴角紧紧地抿着,仿佛从未有过一丝笑容。
他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个同样寒冷的秋夜。
那时的他,还是一个在皇阿玛的目光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皇子。
他通过隐忍和等待,赢得了这场残酷的游戏。
他继承了父亲的皇位,也继承了父亲的制衡之术,甚至将这种权力之术,发挥到了极致。
他做到了。
他成为了一个比父亲更加集权的皇帝。
他为这个国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使得后来的乾隆盛世,成为可能。
但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他失去了亲情,失去了朋友,也失去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他的世界里,只剩下了奏折,权力和无尽的猜忌。
他看着镜中的自己,忽然觉得有些陌生。
他想起了皇阿玛。
他想,皇阿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皇位传给自己,或许不仅仅是因为自己能干,孝顺。
更重要的,或许是因为,他从自己的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
那种为了皇权,可以牺牲一切的冷酷和决绝。
康熙有三十五个儿子,为何多数人不敢和雍正争储?
因为,他们面对的,从来就不是雍正一个人。
他们面对的,是康熙皇帝耗费六十一年心血,打造出的一套完美的,不容挑战的绝对皇权体系。
而雍正,只不过是这个体系最合格的,也是最冷酷的继承者和执行者。
当其他的皇子,还在想着如何用恩惠和声望来赢得人心的时候。
雍正,早已洞悉了这场游戏最核心的秘密。
那就是,权力,不需要赢得,只需要掌控。
他手中的木梳,轻轻滑落。
窗外,月凉如水。
这座辉煌的紫禁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见证了一场最惊心动魄的权力角逐。
而最终的胜利者,此刻,却只剩下无边的寂寞。
大清的江山,在他的手中,会走向何方?
历史,会给他一个怎样的评价?
雍正不知道。
他只知道,这条布满荆棘的帝王之路,他必须一个人,孤独地走下去。
直到生命的尽头。
本篇故事为虚构内容,如有雷同纯属巧合,采用文学创作手法,融合历史传说与民间故事元素。故事中的人物对话、情节发展均为虚构创作,不代表真实历史事件。
国内配资官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配资炒股开户网站风云T11的空间优势堪称同级标杆
-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