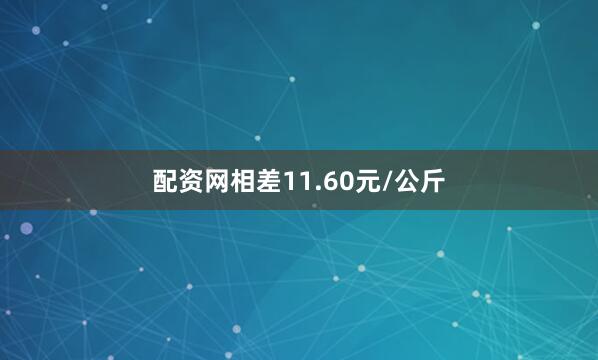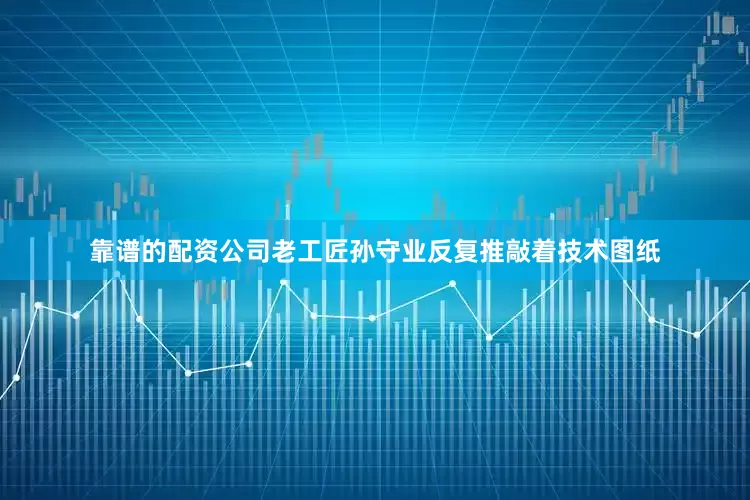胡乔木同志
<文章于1997年初撰写>
胡乔木同志,一位忠贞不渝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与我的年龄相差五载。在延安,我们相识相知,携手共进,虽然时有波折,但总计已有五十余载。他博学多才、笔耕不辍,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那和蔼可亲的形象与音容笑貌,至今仍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
我与乔木先生的相识,始于1941年深秋时节。那时,我自华北根据地返抵延安,参与整风运动,并有幸列席了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乔木先生于那年的春天开始服务于毛主席,与王首道同志一同负责会议的记录工作。他年不过三十,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在会议中,他专心致志地记录,未曾发声。众人皆以“乔木”称呼他,此名前缀以“胡”字,则是自1945年重庆谈判之后的事。
自9月10日起,政治局会议持续召开,直至十月底方才落幕。此次会议的核心在于回顾并总结自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夕的党的历史进程,着重探讨遵义会议未竟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同时在党内坚决抵制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根本上清算王明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九月会议的前后,我们陆续印发了《六大以来》的相关资料。起初,这些资料以散页的形式分发,逐篇阅读,随后则汇编成厚重的册子。
听闻乔木同志曾是主席编纂《六大以来》的要角,担当着主要助手之职。尽管乔木同志对那段历史并无深刻亲历,他却能迅速对搜集到的众多文件进行整理、筛选,迅速理清脉络,将其编纂成册。阅读此书,人们能够清晰地洞察党的历史渊源,对何为正确路线、何为错误路线一目了然。这实属难得的才能。他的出色工作赢得了主席的青睐,亦得到了众人的尊敬与认可。
凭借编纂《六大以来》的丰富经验,继续编辑《六大以前》,以及选编《两条路线》,对胡乔木来说已是游刃有余。他博学多才,精通中外文学,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有深厚的基础。自从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后,胡乔木接触了大量重要的政治事务,并不断得到主席的悉心指导与教育。他对党的历史和马列主义的理解,以及他的文字功底,均远超常人。因此,在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中,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那时他在党内还只是一个年轻的晚辈。据我所知,在弼时同志起草的决议草稿基础上,胡乔木曾修改过一份稿件;最终,毛主席在闻天同志修改过的稿件上亲自润色,胡乔木也协助其中,将主席的重要思想以恰当的文字形式呈现出来。1945年4月,历史决议正式通过,中央委员会中无人不知胡乔木这一杰出人才。到了1951年,党成立30周年之际,撰写一篇讲述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胜利的文章,这一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胡乔木的肩上。他仅用不到一周的时间便完成了这篇长文。胡乔木对党的30年历史早已烂熟于心,自然能够一气呵成。主席审阅后十分满意,建议不再将其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而是以“胡乔木”的名义公开发表。这篇作品便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个人名义发表,并非胡乔木有意炫耀,而是毛主席的决策。正值建国初期,此举效果显著。共产党拥有胡乔木这样一位卓越的笔杆子,即便是对立者也不得不为之赞叹。
“有了乔木,我们就有饭吃。”
进城之后,毛主席委以乔木重任,任命他为新闻总署署长,深信他能够妥善管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在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期间,他的主要职责亦聚焦于新闻领域。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抗美援朝、经济复苏、民主改革以及内政外交等事务纷繁复杂。乔木出色地领导了新闻工作,通过鲜活的现实素材,将亿万人民的思想凝聚,使之与毛泽东思想保持一致。1956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再次指派乔木领导《人民日报》进行改版。在乔木的主持下,《人民日报》焕然一新,摆脱了苏联《真理报》的教条束缚,变得生动活泼,既坚持了党性原则,又很好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愿。乔木笔耕不辍,亲自撰写重要社论,并带头撰写杂文。副刊也办得颇具可读性。据我所知,毛主席曾对那段时期的报纸表示过极大的满意。
自4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我与乔木同志始终紧随主席身边。他最为卓越的成就,不仅体现在新闻领域,更在于参与起草和修订了党和国家众多关键文件。在这些至关重要的工作中,乔木同志无疑是主要撰稿人之一。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经毛主席亲自主持,经过与各民主党派的多轮协商,《共同纲领》得以顺利通过。乔木先生是这份临时宪法的核心起草人。自1954年起,乔木先生负责起草我国的首部宪法,他带领田家英等同事,与毛主席一同在杭州刘庄居住,并在主席的领导下,历时数月完成了这一任务。在此之前,乔木先生还撰写了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内团结的决议。当时,少奇、恩来、小平同志身处北京,他们首先草拟了一份初稿,由我亲自送往杭州。毛主席审阅后,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指示乔木进行修改,并在多处进行了重大调整。那段时间,我往返于北京与杭州之间,几乎每周都要往返一次,传递相关信息。宪法草案完成后,政治局常委们齐聚杭州,对定稿进行了深入讨论。对于这部国家根本大法的诞生,大家的心情都充满了激动与振奋。
1956年,这一年载入史册,见证了我国三大改造的圆满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幕正式拉开。开年伊始,中央隆重召开知识分子大会,总理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然成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并号召大家“投身科学事业”。这份报告出自乔木同志之手,无疑充分体现了中央和总理的深思熟虑。同年之中,我国八大即将召开,这标志着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新征程。乔木同志在此次筹备工作中,协助主席与少奇同志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等关键文件,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八大选举中,乔木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书记处候补书记,成为领导集体中一颗崭新的力量。年底,面对苏共二十大后涌现的反共思潮和思想混乱,乔木同志依据中央政治局的研究成果,执笔撰写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不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更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重要文献。
1957年,乔木亲身参与的、对中苏关系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便是那年的《莫斯科宣言》。当年11月初,毛主席亲自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随即参加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随后的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我和乔木均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参与了此次活动。在我们启程前往莫斯科的前一周左右,苏共中央递交了一份《莫斯科宣言》的初稿,旨在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进行讨论并通过。乔木审阅了这份稿件后,认为其中存在不少问题,遂立即向毛主席汇报,坚决主张必须进行修改。毛主席随后召见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亦认同乔木的看法,认为必须作出修改。于是,乔木便着手对稿件进行修改。当时时间紧迫,但乔木以其高效的文风,仅用两天时间便完成了修改工作,我将修改后的稿件交给了翻译组——阎明复、赵仲元、李越然等同志,他们夜以继日地将其翻译成俄文,并交给了苏方。抵达莫斯科后,双方进行了讨论,苏联方面并未提出异议。乔木所执笔作出的重要修改,后来大多数被正式发布的宣言所采纳。苏斯洛夫甚至提议,这份宣言草案可以由苏中两党共同提交会议。邓小平同志则认为,还是由苏共提交更为适宜。经过进一步的协商,最终宣言草案还是由中苏两党共同提交。当时,苏共面临困境,对我们表示了更多的尊重;我们则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大局出发,强调“以苏联为首”的原则。1960年11月,我和乔木再次随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出席了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此时,中苏之间的分歧已经公开化,乔木在会谈中与苏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众多国内外重大事件中,我对乔木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深感敬佩。他的思维敏捷,文笔锋利且简洁,这在众多从事文字工作的人中实属难得。他拥有独到的见解,敢于向毛主席提出不同观点,甚至与主席展开争论,这一点,鲜有人能为之。因此,他既尝到了快慰,也承受了苦恼。
1959年庐山会议,乔木赞成"成绩讲够,问题讲透,前途光明"的指导思想,对印发彭德怀同志的信,把会议的方向根本改变是有意见的。后期要他起草决议,他不赞成把彭德怀等同志的问题说成是反党集团。他晚上来找我谈过,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反党集团啊。但没有办法,只能服从。1961年他两度到湖南调查,深入到了毛主席的老家韶山,如实地向毛主席反映了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主席采纳他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在农业六十条中,把办公共食堂这一条实际上取消了。在他那个位置上,有许多事情确实也很难办。庐山会议后期,少奇同志同他有个谈话,意思是还要写一个反对"左"的文件。他在当时的空气下,不敢去跟主席说。武昌会议要公布粮食生产数字。这个数字水分较大,陈云同志主张不公布,要他转告主席,他也不敢去跟主席说。三年困难时期,"左"倾的毛病暴露无遗。毛主席怪乔木:为什么不跟我说!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利不报告!凭心而论,那时就是报告了,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乔木受批评后,有点想不通,加之长期劳累,身体本来就弱,结果他的神经衰弱症越来越重,只能长期休养了。
自“文化大革命”爆发起,我便被拘禁。他对我身在何处一无所知,我亦对他的后续生活状况一概不知。时光荏苒,转眼已过十数年,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我们才得以重逢。他以风趣的口吻告诉我,在那场浩劫中,他宛如被“冷藏”了一般。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乔木服务于书记处,而我则任职于军委。自十二大之后,我们双双步入中央政治局,自此,工作联系愈发频繁,相互间的了解也愈发深厚。乔木参与了中央领导层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对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及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确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构建,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被誉为“党内第一支笔”。即便如此,他的主要职责仍旧是为中央撰写重要文件。
乔木同志文集的问世,使得公众得以知晓,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叶剑英同志在国庆30周年的重要讲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二大党章、十二大政治报告以及1982年宪法等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均出自乔木同志之手,在中央的领导下,由他起草与修改而成。乔木同志不仅擅长领会与执行邓小平同志及陈云等领导人的指示,更善于吸纳并综合众人的意见。在研究问题时,他总是深入细致,例如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为强化人民民主,尊重公民权利,他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从第三章提升至第二章。在他的指导下,对全球111个国家现行宪法中关于人民权利义务的章节结构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与统计。他对文辞的打磨亦是众所周知,无论是亲自撰写还是审阅他人文稿,他都反复推敲,直至满意为止。在我们这些前辈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惯例,即重要文稿在对外发布前,都会请乔木同志审阅把关,以确保无误。乔木同志总是来者不拒,全力以赴。
乔木负责统领这一繁复的思想理论战线,我认为他在处理倾向斗争的问题上,表现得恰到好处。回想在十二大召开前夕,一位高级干部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了一篇与大会报告精神相悖的文章,宣扬了“左”倾观点。乔木与我多次商议,克服重重阻力,对这位干部进行了不具名的公开批评。同时,他亦强调,批评文章必须“具备充分的说服力,逻辑严密,言辞得当”。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期,乔木毫不犹豫地发起了斗争。尽管面临来自各方的非议和重重压力,他始终坚定不移,展现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忠诚与坚定。
乔木先生始终关注党史研究机构的构建,并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领导班子组建事宜亲力亲为。1990年夏日,他再次与我及一波同志商议,将国史研究纳入议程,并向中央提出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建议,由力群同志担任指导,旨在一方面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另一方面为日后国史馆的建立奠定基础。在党史、国史以及军史诸多重大问题上,我都与他深入交流,以获取符合实际的见解,并作出适宜的处理。
1991年,乔木不幸患上绝症。他深知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因而更加拼命地投入工作。在加紧撰写关于40年代毛泽东的回忆录之际,为庆祝建党70周年,他还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等杰出作品。那年夏日,他再次在北戴河邀请我共同主持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会议,审阅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他毫不松懈地投入精力,依旧严谨细致,对每个词句、每个标点都精益求精,并亲自增补了诸多关键观点和史实。会议结束之际,他更是倾尽全力撰写了一篇“题记”,以表达对这部书稿的赞誉与期待。他致力于将历史著作的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结合,对辞章完美的不懈追求,令我由衷敬佩。1992年9月中旬,正当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我听闻乔木病危的消息,急忙赶到医院探望。然而,我到达时,他已经无法言语,只能以目光传递情感。我未能亲耳聆听他的最后嘱托,实为遗憾。但我想,他的思想、情感和期望,都已融入他一生所写的无数文字之中。这些文字中,标注他个人名字的只是冰山一角,大部分则是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发表。他个人已经与我们的党、国家、民族紧密融合在一起。这是终生以笔为人民服务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也是我们最应向乔木同志学习的地方。

国内配资官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