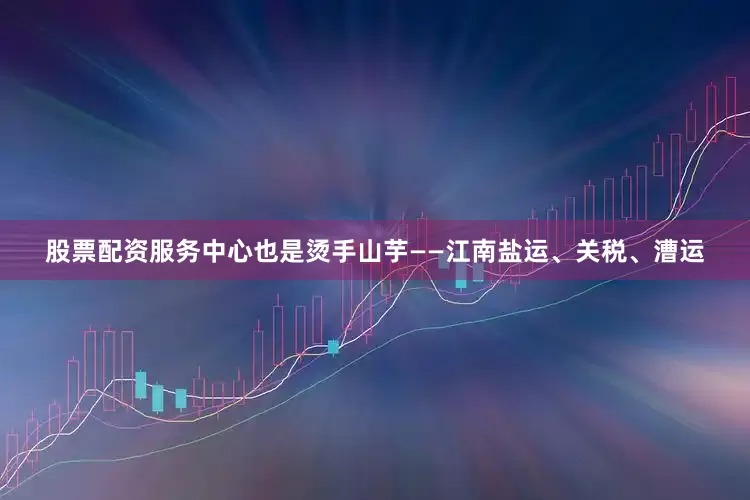
湘军余脉的最后定盘星:刘坤一在废立风波与东南互保中的两次力挽狂澜


湖南新宁,山里雾气重,早晨鸡叫得比别处早。刘家的老宅就在县城边上,青砖灰瓦,不算富丽,但书香气浓。刘坤一小时候常被父亲逼着背《资治通鉴》,背不出就罚去挑水。他原本想着考个功名,当个安稳知县,可咸丰年间太平军一路打到江西,他的堂叔刘长佑来信——不是商量,是直接派人带他走,说是“楚勇缺人”。


湘军营里的日子苦得很。那时他才二十出头,一身书生气,被老兵笑作“纸糊的枪杆子”。可几仗下来,他硬是在泥泞里爬出来了,从江西到广西,一路跟着楚勇打硬仗。有一次攻桂林城,雨夜泥滑,他带的人先翻上去,用火铳压住敌楼,这一役让他在湘军中站稳脚跟。后来有人说,“这小子能打,也能记账”,因为战后粮饷清点、百姓安抚,他都干得妥帖,这在只会冲锋的大队伍里算稀罕货。


光绪年间,两江总督这个位子三度落到他手上,还兼管南洋通商事务。这可是肥差,也是烫手山芋——江南盐运、关税、漕运,全系于此。一旦乱了,北京朝廷银根就断。他治政宽厚,但遇事果决,有案牍留存,说他审大案时一句废话没有,却也不轻易杀人。据苏州府档案记载,有一年江海关贪墨案牵连甚广,本来按律要枭首数人,他斟酌利害,只斩主犯,其余革职流放,让地方士绅心服口服。


甲午败后,大清上下像漏水的船,到处是慌乱声。他在南京坐镇,看着日本人的新式学堂和铁轨修到海边,就有些坐不住了。据说1896年春天,在金陵机器局的一次茶叙上,他突然问随员:“若我辈再迟十年,会不会连造枪的人都没了?”随员愣住,那句话后来被记录进《两江备忘录》。从那以后,新式学堂和译书馆开始多起来,这是外界少提的一笔账。


戊戌变法失败后,宫里的风声传到南京码头工人的耳朵里——要换皇帝?码头上的伙计们只当茶余饭后的闲话,可读书人急了,因为这事儿若真成,不只是北京热闹,全国都会跟着动荡。当时有人劝刘坤一少表态,以免卷入漩涡。但他的奏折还是送到了紫禁城:“废立之议,中外难防。”又亲自北上见慈禧,据传荣禄当面劝他说,“此事已定”,而他只是拱手道:“恐失天下心。”这番阻拦,让光绪虽仍困瀛台,却保住名分,没有引发更大的外交危机。《顺天时报》英文版甚至隐晦地称“两江之意见影响全局”,这是外国记者对他的侧面注脚。

1900年的夏天闷热异常,北京传来的消息却像冰碴一样凉透心:慈禧下诏向列强宣战。不等圣旨抵达南京港口,各国领事已经先找来了,他们怕的是长江口炮台开火、租界遭殃。在上海跑码头的黄包车夫回忆过,那阵子街上的巡捕神色紧张,比往常多了一倍巡逻队伍。这时候,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隔空飞檄,又派密使至汉口,两地很快敲定所谓《东南互保章程》。条款写得直白:保护洋商教会与通商港口,你们别打我们,我们也不动你们。这份协议签好当天,《申报》暗语报道“沪市如常”,但行内都知道,这是刀尖上的平衡术。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八国联军没往南走一步,而苏杭织机照转、广州米市照开。一位英国海关官员私下感叹,“如果没有这种默契,我们可能不得不给更多兵船加煤油”。这一缓,就是几年喘息机会,为沿海工商业保存元气,也为后来新政积蓄财力。有批评者骂他们割据自保,可杭州西湖边卖龙井茶叶的小贩恐怕不会认同,因为战火没烧过来就是最大的福分。

1901年的冬末,他们又递交了一份著名奏折,被称作“江楚三折”:裁科举停武科设学堂奖游学。其中裁撤武科尤其敏感,因为不少绿营将领靠这个出身吃饭。但奏折最终获准,新式教育体系开始替代旧制,这里面有多少博弈,现在史料还理不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从刀丛血影中爬出来的人,会主动推动读书种田的新秩序,并非寻常选择。有老同僚回忆说,“他看重少年习艺胜于练枪。”这种想法放在那个年代,是逆潮流而行的胆识吧。

至于晚年的故事,就淡下去了。据家谱记载,他病逝前几个月,还让人在院中种下一株桂花树,说秋天香的时候请几个学生来吟诗赏月。然而等花开,人已卧病不起。同乡老人讲起这段,总爱摇摇头:“唉,人活几十年,到底图个啥呢?”如今新宁老宅门楣还挂着木刻匾额,上面两个字已模糊,看仔细才认出是“持正”。或许,那就是他的底色吧,无论救谁,也是为了守一个正字罢了。

内容来自公开资料与个人见解,仅供学习交流,不构成定论或权威史实参考

国内配资官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